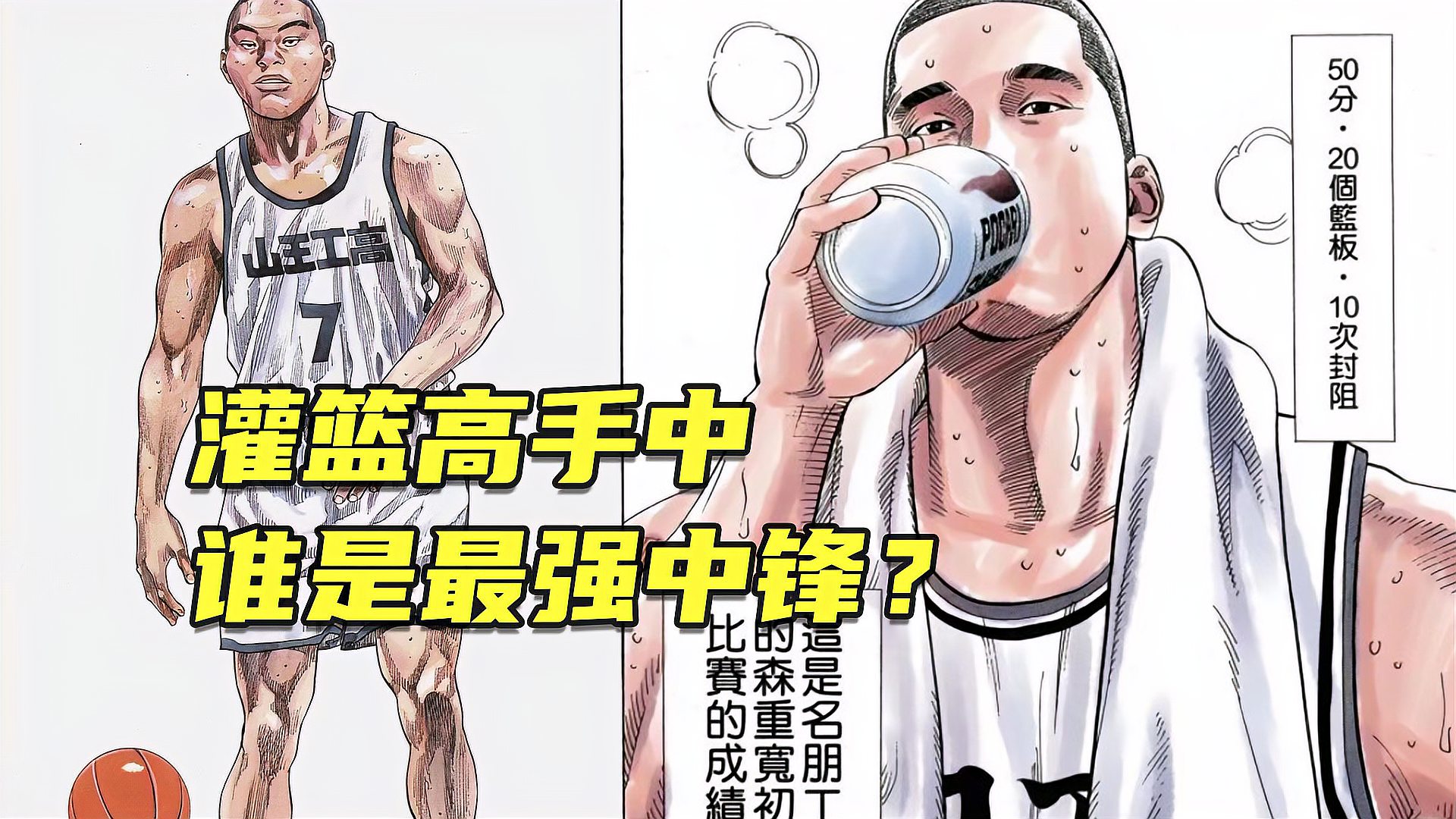从松本清张的砂之器,森村诚一的人证,再到东野圭吾,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实际形成一个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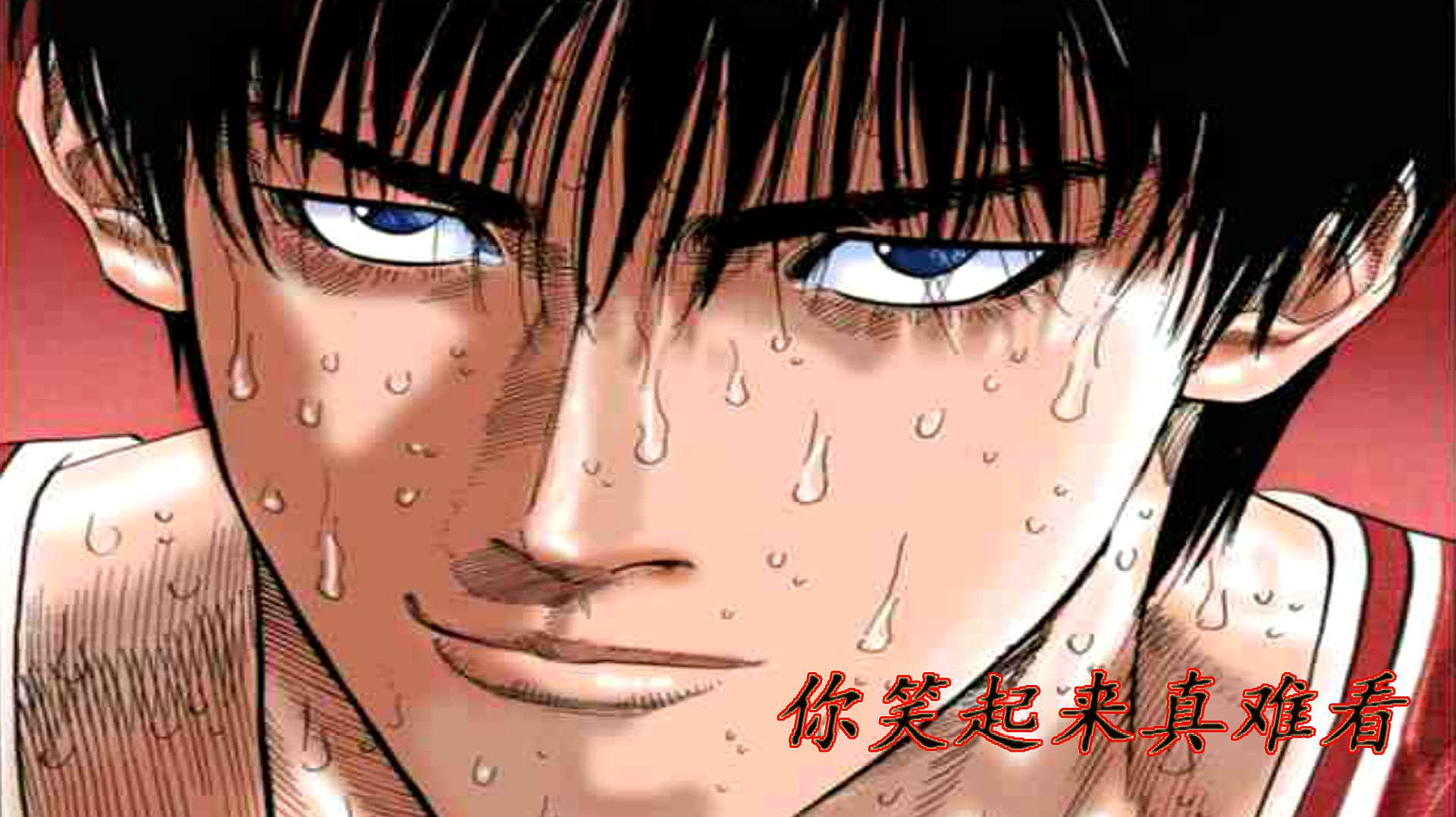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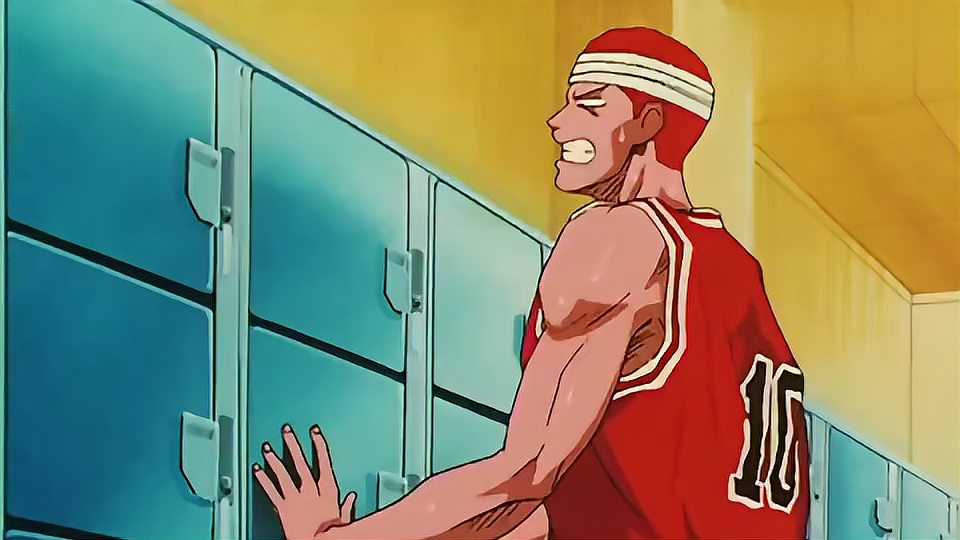 想起皮亚维奥利的生命三部曲,恍然大悟这部电影差在哪里.
想起皮亚维奥利的生命三部曲,恍然大悟这部电影差在哪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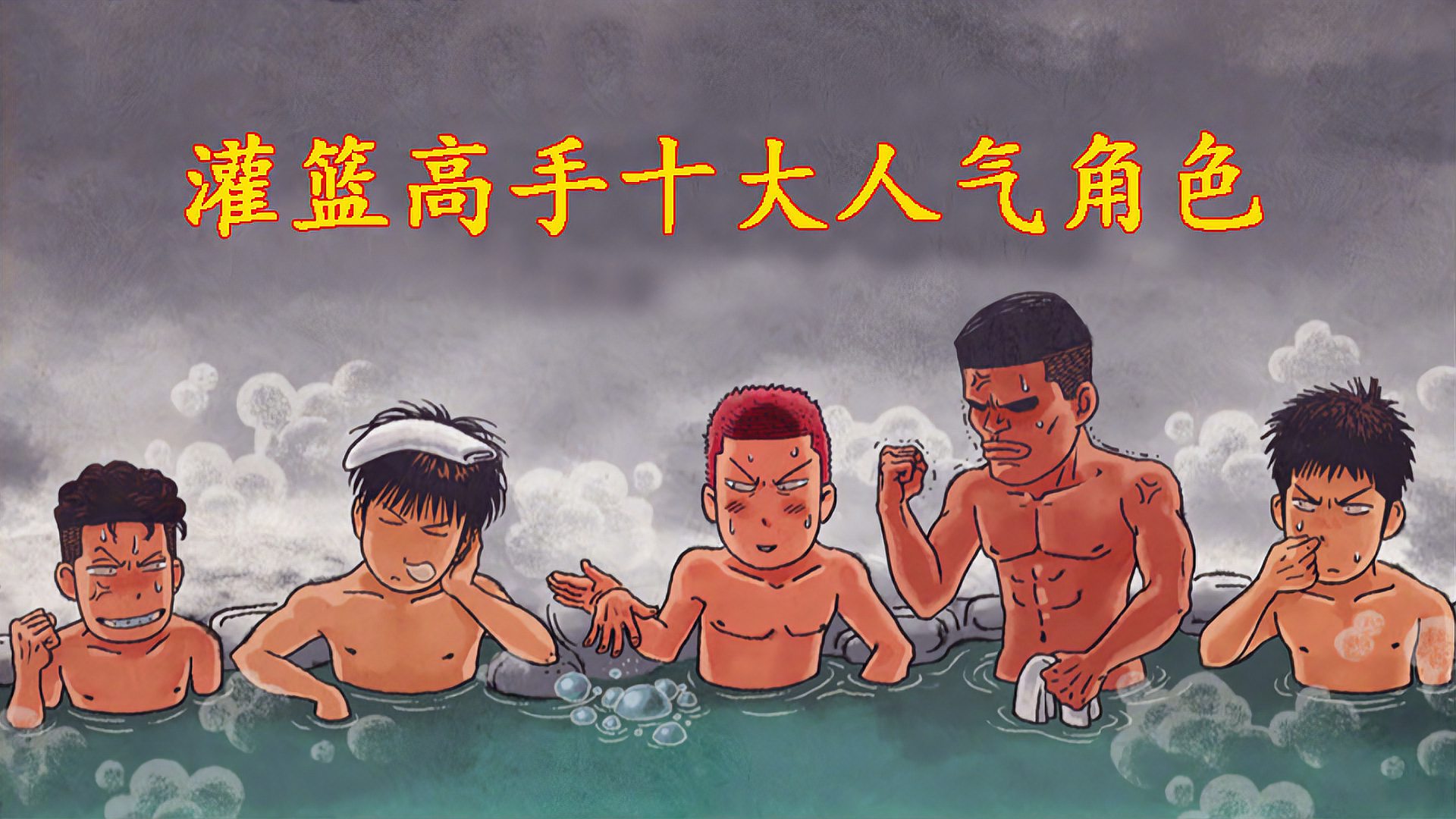 为了尽可能好看,剪辑和摄影排布出了动人的家庭亲情,但这不是纪录片的本质,摄像机纯粹的沦为了工具化应用.
为了尽可能好看,剪辑和摄影排布出了动人的家庭亲情,但这不是纪录片的本质,摄像机纯粹的沦为了工具化应用. 四个春天的片段,可能大部分观众看完了收获的只是动人的家庭日常,而生命无常的窥悟和家庭隐秘的一面都被隔断了.
四个春天的片段,可能大部分观众看完了收获的只是动人的家庭日常,而生命无常的窥悟和家庭隐秘的一面都被隔断了. 观赏它会让人感动和愉悦,但是作为一部电影的影后反思,他是一部不成熟的电影,作为家庭私影像纪录片人物只有了“动”(行为动作)而没了私(内心深层的记录),况且摄像机暴露的也太多了,想起小口袋看过的《灌篮高手》系列就抓住了“私”这个点,纪录片的每一个题材的元素其实都很明显,如果不能产生连续性,那就是跨越了纪录片的界限,甚至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是枝.
观赏它会让人感动和愉悦,但是作为一部电影的影后反思,他是一部不成熟的电影,作为家庭私影像纪录片人物只有了“动”(行为动作)而没了私(内心深层的记录),况且摄像机暴露的也太多了,想起小口袋看过的《灌篮高手》系列就抓住了“私”这个点,纪录片的每一个题材的元素其实都很明显,如果不能产生连续性,那就是跨越了纪录片的界限,甚至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是枝. 而四个春天处于这样一个边界不伦不类的特质越发明显.
而四个春天处于这样一个边界不伦不类的特质越发明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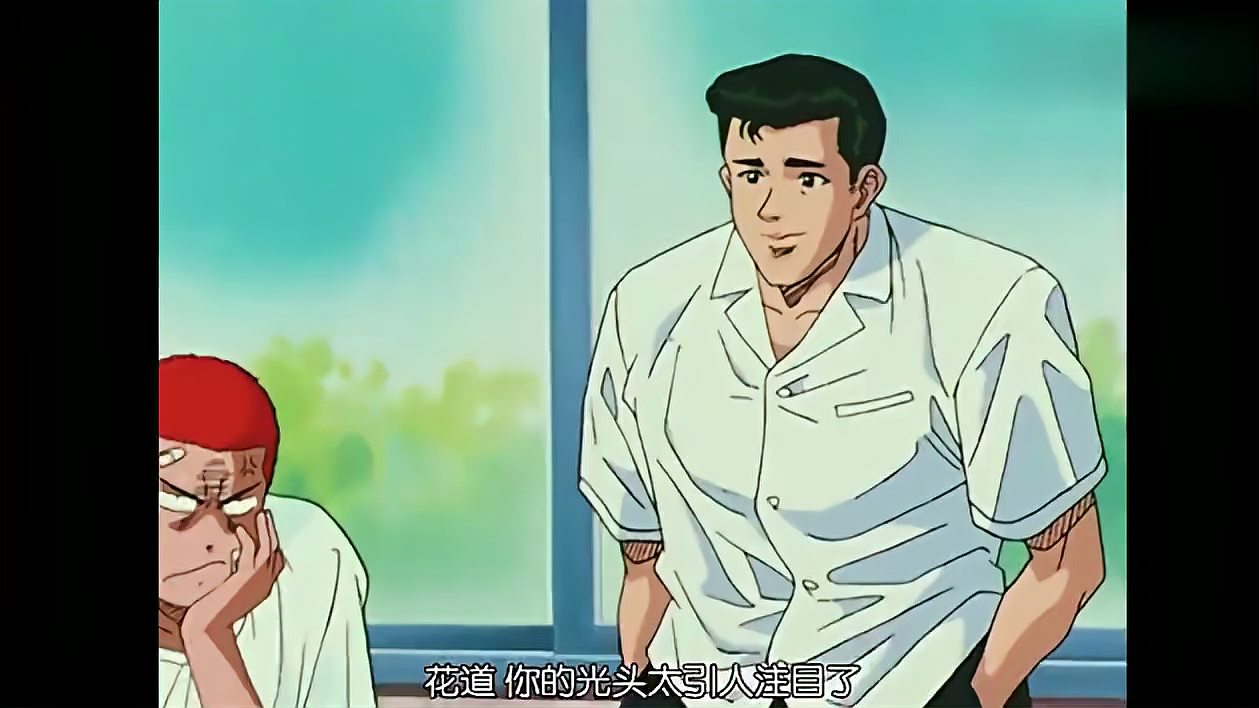 但仍然感谢陆导让我们重温思乡之情.
但仍然感谢陆导让我们重温思乡之情.